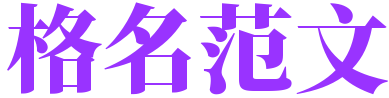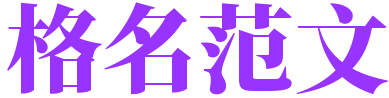少年不识愁滋味,爱上层楼,爱上层楼,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而今识尽愁滋味,欲说还休,欲说还休,却道天凉好个秋。要勉强说愁,则感情是虚伪的,空洞的,写出的东西,连自己都不能感动,如何能感动别人呢?

我的意思就是说,千万不要勉强写东西,不要无病呻吟。即使是有病呻吟吧,也不要一有病就立刻呻吟,呻吟也要有技巧(我挺喜欢这句的,呵呵)。如果放开嗓子粗声嚎叫,那就毫无作用。还要细致地观察,深切地体会,反反复复,简练揣摩。要细致观察一切人,观察一切事物,深入体会一切。在我们这个林林总总的花花世界上,遍地潜伏着蓬勃的生命,随处活动着熙攘的人群。你只要留心,冷眼旁观,一定就会有收获。一个老妇人布满皱纹的脸上的微笑,一个婴儿的鲜苹果似的双颊上的红霞,一个农民长满了老茧的手,一个工人工作服上斑斑点点的油渍,一个学生琅琅的读书声,一个教师住房窗口深夜流出来的灯光,这些都是常见的现象,但是倘一深入体会,不是也能体会出许多动人的涵义吗?你必须把这些常见的、习以为常的、平凡的现象,涵润在心中,融会贯通。仿佛一个酿蜜的蜂子,酝酿再酝酿,直到酝酿成熟,使情境交融,浑然一体,在自己心中形成了一幅成竹,然后动笔,把成竹画了下来。这样写成的文章,怎么能不感动人呢?我的意思就是说,要细致观察,反复酝酿,然后才下笔。
创作的激情有了,简练揣摩的工夫也下过了,那么怎样下笔呢?写一篇散文,不同于写一篇政论文章。政论文章需要逻辑性,不能持之无故,言之不成理。散文也要有逻辑性,但仅仅这个还不够,它还要有艺术性。古人说:言之无文,行之不远。又说:不学诗,无以言。写散文决不能平铺直叙,像记一篇流水账,枯燥单调。枯燥单调是艺术的大敌,更是散文的大敌。首先要注意选词造句。世界语言都各有其特点,中国的汉文的特点更是特别显著。汉文的词类不那么固定,于是诗人就大有用武之地。相传宋代大散文家王安石写一首诗,中间有一句,原来写的是春风又到江南岸,他觉得不好;改为春风又过江南岸,他仍然觉得不好;改了几次,最后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,自己满意了,读者也都满意,成为名句。绿本来是形容词,这里却改为动词。一字之改,全句生动。这种例子中国还多得很。又如有名的鸟宿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,原来是僧推月下门,推字太低沉,不响亮,一改为敲,全句立刻活了起来。中国语言里常说推敲就由此而来。再如咏早梅的诗:昨夜风雪里,前村数枝开,把数字改为一字,早立刻就突出了出来。中国旧诗人很大一部分精力,就用在炼字上。
我想,其他国家的诗人也在不同的程度上致力于此。散文作家,不仅仅限于造词遣句。整篇散文,都应该写得形象生动,诗意盎然。让读者读了以后,好像是读一首好诗。古今有名的散文作品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这一个类型的。中国古代的诗人曾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理论,有的主张神韵,有的主张性灵。表面上看起来,有点五花八门,实际上,他们是有共同的目的的。他们都想把诗写得新鲜动人,不能陈陈相因。我想散文也不能例外。我的意思就是说,要像写诗那样来写散文。( 文章阅读网: )
光是炼字、炼句是不是就够了呢?我觉得,还是不够的。更重要的还要炼篇。关于炼字、炼句,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著作中,也包括大量的所谓诗话,讨论得已经很充分了。但是关于炼篇,也就是要在整篇的结构上着眼,也间或有所论列,总之是很不够的。我们甚至可以说,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文人学士足够的重视。实际上,我认为,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。
季羡林,字希逋,又字齐奘。著名的古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东方学家、思想家、翻译家、佛学家,作家。他精通12国语言。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、北大副校长、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。或许在他头上的光环太多太多,然而我最感动于的是他为人为学问的严谨态度,做人是永远说不尽,说不透的话题,学问更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骄傲。作为一代国学大师,我觉得从他身上学到一些皮毛,都足够现一代许多自称作家的人受用一身的。遑论一些根本不了解散文是什么,却大笔一挥,不吝啬笔墨的人了。连季老这样生活阅历丰富,一生大起大落的巨匠都觉得没有那么多感情去抒发,我搞不懂为什么现代的一群年轻人哪来那么多的情感毛发呢?
我觉得散文贵在真情,有哲理,有对生活对社会对人生的些许思考。纯情感的散文不叫散文,叫呻吟。
有好多文章是大可以不必写的,有好些书是大可以不必印的。如果少印刷这样的文章,出版这样的书,则必然能够少砍伐些森林,少制造一些纸张;对保护环境,保持生态平衡,会有很大的好处的;对人类生存的前途也会减少危害的。
不知道说这些对有些人有多少意义,因为中国人本就倾向于美的靡费,既于他人无碍,何妨用以自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