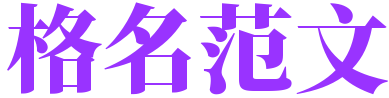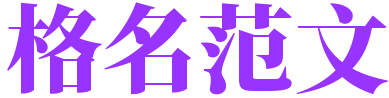“叮铃铃——”讨厌的电话,我别过脸去,懒得去理。
“叮铃铃——”我一对儿女都在广东打工,恐怕是他们打来的。我只得仄转身,伸出一只手,李专干赶快把话筒递了过来。

“喂——”我对着话筒拉长了声调。
“喂,是王书记吗?我是党政办小周,我说,我说”这个家伙竟然油腔滑调,鹦鹉学舌。用“我说”这两个字作讲话的开头,是我的老毛病。
“我说,啊,什么‘我说’,小周呀,我累得不行,你有屁就放吧”我有点不耐烦了。
“对不起,王书记,我不是开玩笑。奉汤书记指示,请你和刘村长明天上午到乡政府斩第一季度的税款。”
“知道了”我重重地撂下话筒,大家都看着我。为掩饰自己的失态,我装糊涂地闭上眼睛。
此事糊涂不得呀!“嗨!”我大呼一声,拍了一下脑门。大家又把视线转向我,我的脑子快速反应着。前几天,汤书记就一季度税款一事已给我打了招呼,因烦琐事太多了,我还没有向大家传达。第一季度是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二十五,汤书记还嘱咐我要超额完成。超额个屁!就是这一万元还八字没有一撇呢。没办法,赶鸭子也得上架,他们原来说今晚要“三打哈”,轻松几个小时,也轻松不起来了。我抓住靠椅扶手猛地坐了起来,大喊:“我说老婆,快点办饭。”
“我说,是这样啊”我的困意全无,眼光扫视了他们一遍,说:“今天晚上我们四个人要搞一万元钱,明天上午我和刘村长要去斩税帐。我说,吃完饭后,各自到分片的组找组长要钱。这样吧,我和村长每人不得少于三千,你们两个每人不得少于二千,就这样办!”
吃完饭,我大步流星地去了组长老江家。老江为人耿介,而且前几天我已经发信给他了,想必他已是万事俱备,只等东风把我吹进屋。他把我让进屋,倒了一杯米酒。我呷了一口酒,直奔主题:“我说老江,税款准备得怎样啦?”
“喝酒,喝酒,就和你来结”老江转身进了房,一会儿手里就摇晃着一张纸出来了。
“我说你呀,不要算数了,你给我钱就是了,明天我到乡政府回来再和你结清楚。”
“要得,这也是钱嘛”他双手把纸条递了过来。
“什么?”我把眼睛瞪得圆圆的,纸条上白纸黑字:“今欠到,二零零零年下半年米粉款壹仟伍佰元整。乡政府食堂,刘大发。”
我知道,刘大发是承包乡政府食堂的农民。“我说,他欠的钱为何要我村里去讨?”我提出了质疑。
“听说政府干部已有半年没领工资了,吃饭没钱就只有挂数。老刘不便一个个去找干部讨,欠米粉店的钱就变成了欠条。”
“啊,我说,他米粉店老板这又是什么意思?”我恨得咬牙切齿,每次乡政府都要现款,没有钱逼牯牛也要下崽。这个该死的东西,明天就叫他滚蛋!
老江却是慢条斯理:“米粉店开在我们村,用的是我村的电。他的米粉钱不得到手,就拿这张欠条抵了电费。农电员是我组的,他电费收不到,前两天没电费交,农电站就停了我村的电。书记呀,你真是日理万机,贵人多忘事,那天是你要农电员到我这里拿税款代交的电费,农电站才送电。”
“我说,你不要讲了”我听得脑壳都快要散架了,霍地站了起来,把一杯酒一饮而尽,接过这张欠条,又马不停蹄去了另一个组长家。
这个组长交的税款更玄。乡政府去年建办公楼,建筑包头是这个组的,几乎每家每户都去做了工。办公楼半途而废,农民的工钱不能少,组长去收税款,各家各户都拿这个工钱条子抵。
我拿着这一沓欠条回了家,他们还没有回来,估计也好不了多少。据我知道,两个义务兵已有两年没有从乡政府拿到一分钱优抚款了,还有一个育龄妇女乡政府辙区并乡前收了两千元计划生育押金,几年来她一直没有养崽,好久就嚷着要退。汤书记说皇粮国税,各级任务压头,必须解现款,任何条子都要压到下一次。可是,这样的话我已听过不下十次了。我接了这三千多元的条子,而且不记得告诉他们也不要接条子。其实,告诉他们又有什么用呢?钱在老百姓的口袋里捂得热热的,你要得到它,一定要取之有道。而且,这些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,他们等着这个钱过年,看病,建房,送小孩读书。你应该给他的钱分文不给,却还要问他要,于心何忍?“当官不为民做主……”我哼起这几句歌词,心情也轻松多了,他们回来还是要打几盘“三打哈”!
哈哈,我说,管他呢,明天上午这些零零碎碎的碎帐,我都要硬着头皮和政府斩清楚!